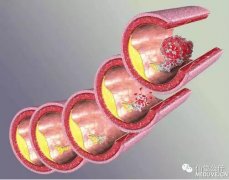于是肠泌素的概念在三十年后被如获至宝地重新捡了回来。和巴尔医生的时代不同的是,此时的科学家已经有了更好的研究手段,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之前讲过桑格蛋白质测序法。于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开始了从小肠分泌物中寻找传说中的肠泌素分子的竞赛。
很快,两种符合“肠泌素”定义的蛋白质分子被找了出来。
它们分别被命名为GIP(gastric insulinotropic peptide/葡萄糖依赖性粗胰岛素分泌多肽)和GLP-1(glucagon like peptide-1/胰高血糖素样多肽-1)。
读者们尽可以忽略这两个佶屈聱牙的名称,我们只需要知道,GIP和GLP-1两个蛋白质,都是从小肠肠壁细胞分泌并进入血液,都能够刺激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就足够了。
这两种激素接近完美地解释了口服葡萄糖的古怪后果:葡萄糖进入小肠后能够刺激这两类激素的分泌,从而更好地刺激了胰岛素分泌和血糖的下降。
兴奋不已的科学家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能不能用GIP和GLP-1治疗二型糖尿病(它们显然不能用来治疗一型糖尿病,因为一型糖尿病人根本没有贝塔细胞可以被刺激)?
毕竟两者和胰岛素一样,都是人体天然合成的蛋白质,安全性应该没问题。同时,对于二型糖尿病人而言,如果能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至少应该能够稍微缓解机体对胰岛素响应能力的下降,从而起到治疗的效果。
这时候巴尔式的失败又一次降临了:将GLP-1持续透析进入糖尿病患者体内的效果确实不错。但是注射GLP-1的效用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微乎其微,几乎没有什么临床意义。
不过这一次,有更好的蛋白质定量技术,人们很快地找到了原因所在(也正是为什么巴尔的实验长久以来无法被重复的原因):GIP/GLP-1在体内会迅速地被分解并通过肾脏排出,其半衰期只有惊人的一两分钟!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神奇的药也来不及唤醒胰岛素从而降低血糖啊。
肠泌素及其治疗糖尿病的希望,是不是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了?
没有,没有。
别忘了我们刚刚说的,“不合常理”的观察结果,往往是美妙发现的前奏。正因为这个令人沮丧的发现,肠泌素的故事从此进入快节奏,和命运多舛的二甲双胍分道扬镳。
“理性”制药和利拉鲁肽的诞生
肠泌素能被我们的身体降解这一发现,迅速为科学家们指明了一条能够摆脱“炼金术”,“理性”开发糖尿病药物的光明道路。
读者们不妨暂停阅读,给自己布置一点点思维体操的作业。如果你是药物开发者,该怎么利用这一个初看令人沮丧的发现呢?
一方面,肠泌素(特别是GLP-1)确实有很好的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效果。而另一方面,注射肠泌素仅有极短的生命期,难以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
那么看起来,是不是至少有两个办法能解决问题?
一个可能性是有意识地修饰和改变GLP-1的结构,让它变得更“皮实”一点,不太容易被身体降解和排出;另一个可能性则是釜底抽薪,干脆找到身体里到底什么物质负责降解GLP-1,把它给抑制了不就行了?
从这两个思路出发,读者们也许能开始感受到所谓“理性”制药的含义。
在这里,我们不再需要依赖意外的观察和偶然的发现(比如山羊豆能够毒死牲畜)来提示我们某种潜在药物的存在,我们可以根据对生命现象的认知,主动地、有意识地去创造出我们需要的药物来。
先说说这前一个思路吧。目标非常明确:我们已经知道GLP-1这种肠泌素能够刺激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我们需要的是尽可能的延长它在体内的半衰期,使其充分发挥功能。按照“炼金术”的思路,科学家们和药物开发者们大概需要在野外到处踅摸奇怪的现象,指望不定哪一天能从某种神秘动物的体内找到一种“恰好”可以在人体内活的久一点的GLP-1。
事实上人们确实也这么做了,第一种类似GLP-1的药物正是从一种从有毒的蜥蜴中发现的蛋白质,人们发现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要比人类GLP-1长得多,于是就移花接木地拿它治疗二型糖尿病。
而利拉鲁肽,全世界第二个上市的类似GLP-1的药物,则更好地说明了“理性”制药的特点。和第一种类似GLP-1的药物不同,利拉鲁肽是人类原生GLP-1的衍生物;它也不是来自漫无目的地寻找,而是来自实验室中目的明确的设计。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长话短说,利拉鲁肽的设计充分利用了科学界对GLP-1的各种研究成果。
人们知道,GLP-1是一个由三十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它之所以有着短得惊人的半衰期,是因为它在体内很容易被蛋白酶切割,并随即进入肾脏并被排泄。
因此,想要延长GLP-1的半衰期,关键是防止它被蛋白酶切割。
与此同时,人们通过对胰岛素的多年摸索,已经发现如果在蛋白质分子上连上一段长长的脂肪链,就有可能抵抗蛋白酶的进攻,延缓蛋白质被切割降解的速度。事实上一部分长效胰岛素就是根据这个思路制造出来的。
结合这两条,科学家们就可以大批量地尝试对天然GLP-1进行改造,特别是在30个氨基酸的基础上增加脂肪链,以期制造出能存活得更久的GLP-1类似物了。
可是拿到那么多类似物之后,怎么知道哪种真的有效呢?总不能每种都拿来往人身上注射了看效果吧?
而人们同时也知道,GLP-1之所以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是因为它能够特异地结合胰腺贝塔细胞上的受体蛋白。
因此,拿到一系列类似物候选分子之后,药物开发者们只需要在试管里检测这些分子和GLP-1受体的结合强度,就能够很好地预测哪种候选分子效用强劲了。
就是这样,2000年,诺和诺德公司的科学家们第一次报道了利拉鲁肽的合成和基本特性。在之后的十年中,利拉鲁肽经受了严苛的临床检验,并最终于2009和2010年在欧洲和美国上市(2011年在中国上市)。而就在今年,利拉鲁肽还在美国市场获得了作为肥胖症药物的资格。
笔者不是临床医生,也无意评价任何一个糖尿病药物的具体临床表现。笔者想展示给大家的,更多是一个摆脱了“炼金术”色彩的药物开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药物开发者们在一开始就设定好了清楚的目标,通过理性的实验设计和临床验证,最终推出一种革命性的新药。
而读者们不应该忽略的是,许多代科学家们对人体奥秘的探索,一步步奠定了理性制药的基础。一百年来,来自实验室的发现,证明了激素的存在,提示和最终发现了神奇的肠泌素,揭示了GLP-1促进胰岛素分泌的原因,发现了GLP-1被迅速降解的秘密……
这些人类最聪明头脑的智慧结晶,最终使得利拉鲁肽的到来显得如此的水到渠成。
药物设计与锁匠的游戏
在试图改造GLP-1,让它变得更皮实和经久耐用的同时,人们还在尝试另一种“釜底抽薪”的制药思路。
既然GLP-1在体内半衰期极短,很容易被蛋白酶切割和降解,那么何不找出罪魁祸首是哪种蛋白酶,干脆将它破坏或者抑制掉?
这个思路说难不难,说简单却也没有那么简单。
说它不难,是因为早在1993年,人们已经知道了GLP-1是如何被降解的。
德国基尔大学的科学家们发现,GLP-1能在试管里被一种名叫二肽基肽酶-4(DPP-4/dipeptidyl peptidase-4)的蛋白酶切掉一端的两个个氨基酸,从而失去活性。这一发现也很快被动物体内的实验所证实。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能找到一个办法,破坏掉DPP-4蛋白酶的活性,就能够延长GLP-1在体内的作用时间,从而达到治疗二型糖尿病的目的。
事实上,从DPP-4对GLP-1的切割功能发现的那一天开始,学术界,工业界的各路神仙就开始了针对DPP-4的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