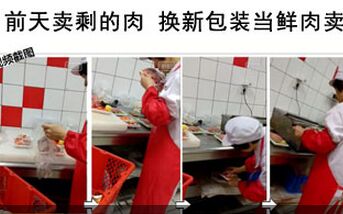在日常生活层面,古人一直是强调士贾同道、义利相合的。士应重视财富,商人则应重视道义。明代东林理学家顾宪成即有过这样的看法,说富,并不足讳。富而好礼,可以提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以泽物。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新的“义利”关系论:“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而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两成,通为一脉。 ”(《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
而社会上对这种态度的实践性行为,则比这些儒者的理论阐发还要实在。比如古代许多行业,如典当、信贷、票号、钱庄等,多有严苛的行业伦理,以强调其基础就在信用二字。明儒唐枢有一同宗的侄子打算经商,苦于没有资金,就与唐枢商量。唐枢对他说:“汝往市中问许多业贾者,其资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诸富人者乎?”他的宗侄就去了一趟市场,并作了调查,回来告诉唐枢:“十有六七是从富人那里借来的资本。”唐枢就说:“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负之尔!未暇求本,先须立信;信立,则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矣。”信用,原本只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而在此已被视为商人的精神。
古代的商业家族对此讲得更加具体,如徽州《新安家族商训》说:“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斯贷,不以牟取为贷,以义为贷;斯典,不以情念为念,以正为念。”徽商是讲朱子学的,其特征是以宗族作为联系,以“孝”道、“恕”道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商训正是儒家伦理的体现,以义生利。
还有,你看晋商,那些票号的名字就反映了儒家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如:志成信、协成乾、世义信、锦生润、恒隆光、徐成德、大德通、大德恒,等等,以义、德、诚、信、厚、公、合等字词,宣示出信义与利益结合的思想。
义利之争,年深日久,只在轻利重义的前提下,我们每以口舌之争,将利的含义拘执于 “为小利益而放弃大义”这样一个狭窄的角度。而自经济的视角而言,思路则会清晰得多。以今日的商品社会为背景,重提古典的义利之辨,有何重要意义?
学界在讨论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时,有个著名的“韦伯论断”。因为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与基督新教伦理相关的;中国和印度没有这种伦理精神,故开展不出资本主义。学界有关韦伯论题的争议,汗牛充栋,意见纷如。但争论之焦点大抵在于儒学能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且隐隐然含有能发展出才是好的意思。而我想回到商业活动本身来探讨。人类自古就有商业,中国也是,不是资本主义出现了才有。殷朝又称商,殷人即是商人,当时贸易已南采南海之珠贝、西伐昆山之玉石。后来之发展,华商更是由纵横欧亚大陆和东亚、南洋、印度洋,而到如今遍布世界。所以应该讨论的是一种商业行为的总原则,局限于近两三百年的资本主义,眼界何其小?
何况,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精神的方式,就是在勾勒经济活动背后之伦理因素。其本身就已点出了经济活动的内核即是“义”,是在义的驱使下才有各种不同的经济行为。只不过,义者宜也,各民族各时代各自合宜的精神有些不同罢了。
所以我们还应回到 《易经》,重新思考“利者义之和”。想想这句话该如何理解。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首先,从事商业,当然是为了谋利。但从事什么样的商业,其选择本身却是义的判断。
这个义,一指价值、道义,二指合宜、适当。譬如贩毒、走私、卖假药、印假钞、放高利贷、做黑心食品,赚钱都是又多又快的,但你会犹豫做不做,这就是义的判断。通常的考虑都是平衡的:是不是既可让自己赚到钱,又满足了社会需求,有益于人?这就是“和”,两者取得了和谐。
其次,商业是交换行为之一。交换,指我拥有某物,有条件地转让给你。整个行为包含三部分的正义问题:
一、我如何拥有该物,程序为何?该物是否可被占有?这涉及“获取正义”的问题。
二、持有物之转换过程为何?是自愿、赠送、竞争、垄断、替换、诈欺,还是买卖?这涉及“转让正义”的问题。
三、以上两者中任何一个出了纰漏,都会引出“矫正正义”的问题。是处罚不正义者,还是修改游戏规则?是法律矫正,还是可以动用私刑去报复?任何一桩商业买卖,之所以能形成利益或利润,其实都须符合这些条件,所以才会说“利者义之和也”,是各种正义的综合结果。换言之,利者义之和或以义兴利,乃是一切商业活动的总原理,任何时代、任何形态的商业都不能背离它。自以为聪明的人,别出妙巧,以为可以获利;甚或耻笑儒家迂腐,以自鸣得意,其实都只是自寻烦恼,以身发财罢了。
简历
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 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听姚中秋教授说士君子的二十世纪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
——典出《吕氏春秋》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路恰巧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了河里,就跑过去,把孩子从河里弄上来了。对子路来说,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件义不容辞的事,不值得一提。结果小孩回家后,跟家长说,我刚才掉河里了,差点淹死了,那个叫子路的救了我。家长一听,这得感谢呀!用什么感谢呢?就把家里那头牛送给子路吧。子路实惠,竟然把牛收了。更怪的是,他收了牛,老师还表扬他。
子曰:打今儿个往后啊,这个鲁国人哪,一定会争着抢着去救落水者的。
子曰:由啊,你这个牛收得对呀。
20世纪初,由于清末推行新政,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朝的覆亡,这一套体制就中断了。士君子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慢慢地消亡了。核心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于中国古典教育传统的中断。当然,这个中断与政治的剧烈变化有极大的关系。国家积弱积贫,政府图富强,所以更相信权力的作用,更相信技术的力量。所以中国的教育,在整个20世纪都是以高度专业化、实用化为目标的,各种学校,多具有高等技校之功用。要建海军,就办一个海军学堂,要搞轮船,就建一个船政学堂,要修铁路,就办铁路学堂,要推行法制,就办了一个京师法律学堂。整个20世纪的教育,就是从这样一个思路发展出来的。其优势在于专业技能的培养,而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就在于,缺乏德行的养成,其所培养的人才,不再是士君子。而只是一些学有所用的专业人才。在这些专业人才中,会有少部分人,比较关注公共事务,他们就成为了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思考现代知识分子兴起这个问题时,会注意到的一个现象。知识分子的兴起,应该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1905年废科举之后,年轻人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0年之后,到1915年,这批人也都大学毕业了,成为了专业人才。他们中间有一批人比较热衷于公共事务,有家国情怀,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由此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需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现象,儒家士人不是知识分子。尽管表面上看,他们有若干相似之处,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社会文化群体。他们所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现代知识分子学的是专业知识,士君子是读经出身,其德行的养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士君子当然也有专业知识,但专业知识对他不重要,其根底是一种心志。而知识分子与此相反,他首先有的是专业知识,然后才是一种情感,一种家国情怀。他没有养成足够的德行,也没有领导者的心志。知识分子习惯于站在社会之外看问题,士君子则是站在社会之内看问题。因为士君子本身即是社会的领导者,出了问题他会反身求诸己。他面对社会问题,首先会反省自己有没有问题,要改造社会,先从改造自己开始。社会上出现了不良现象,我首先反省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不良现象。可是知识分子通常会自我标榜为一个批判者,是站在外面评估一个对象,所以才会面对社会问题指手画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所发出的呼吁往往是要求人们按照他说的来做,他给社会提出要求,让社会改正。他不会因为社会问题而反省自己,问题是社会的,根源在于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办。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姿态,人们因此名之为“姿势分子”。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永远没有让他满意的现实,而真理永远掌握在他自己手里。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义正词严地提出了国民性改造这样一个命题,而一个儒家士君子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儒家士君子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却要执著地改造人民,为人民传授真理。知识分子把自己想象为黑暗中的明灯,拿着手电筒为人民照亮前程,而儒家士君子却要与人民一起在黑暗中摸索。尤其在中国,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士君子所接受的知识往往是一以贯之的,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而知识分子的知识却都是来自西方的。这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就知识分子的本质而言,他们都是反中国文化的,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