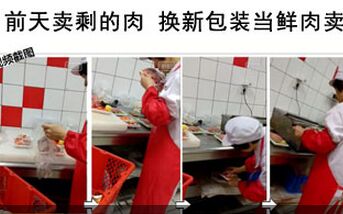“义利之辨”,作为儒学公案,其争议由来已久。后世儒者坚持的根本原则,每不出“重义而轻言利”之范围。董仲舒即说过,君子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比较直接:儒以义为利。以下为本报记者薛百成对龚鹏程教授的专访。
今人说义利,所在皆是义利二分,义在其先,而后可言利。而论二者具体关系,每多飘浮语,顾左右而言他,诸如必须、应该,但是也不能绝对地,也要看到,之类。龚先生所言,似仅此一见,直说儒家如何以义为利,而不说义在利先,不说见利不忘义。
这个是有出处的。 《大学》有言:“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
《大学》教导我们的,正是治国理财的大道理。可惜后世多只注意它前面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部分,在那里吵来吵去,对此就不免轻忽了。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生财有大道有小道,小道是以利为利,大道是以义为利;发财有两种,一种以财发身,利用财来发显自己;一种以身发财,像我们现在这样,拼命赚钱,想发财,结果把自己殉给了财。
孔夫子也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样的话,以表明如不失义,我亦求其利。 《吕氏春秋》中还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放在今天,这就是说助人为乐,报酬也是可以有的。那么这个儒家轻利重义的印象是怎样出现的呢?
儒家本来重视利,且认为利是与义相关联的。既如此,为什么后世老有儒家只谈义不谈利的印象呢?这是孟子的影响。
《孟子·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
此即所谓“义利之辨”,是后世儒者坚持的根本原则之一。董仲舒即说过:君子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人往往奉此为座右铭。可是孟子这句话容易引起误解,令人讳言利,只知高谈仁义。殊不知孟子当时乃是当头棒喝之说、冰水浇背之言,意思是不可仅着眼于利,需由仁义行,才能真正获利。
义利概念自提出,即是为着解决其时道德准则与财富(含富国强兵之大与个人财富之小)之间的矛盾。利,自然指的是财富以及利益,而义则是道德方面的天然约束,但是后世的论争日趋复杂,且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把问题集中在单一的道德层面了。这正如龚先生所说,近人论儒家,主要是从政治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方面论,很少由经济方面去讨论。
由经济方面去讨论儒学,这个话题其实早在100年前就有康有为弟子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大开论域了。康有为写过 《物质理财救国论》,陈氏受其影响,故专就经济方面弘扬孔教。该书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著作,也是迄今影响最大的一部。因为其后的儒家学者多不娴经济学,儒家又被视为现代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故几乎没有赓续的讨论。
这本书是陈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由该校正式出版。可见水准颇获好评。出版次年(1912),梅纳德·凯恩斯就在《经济学杂志》上撰写书评;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也把它列为重要参考文献;熊彼特之名著《经济分析史》亦承认其重要性。
您刚才引用《大学》中有关义的论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是在治国的层面陈述义之要旨。而这一陈述在今人看来,似乎有些飘浮,因为依照我们对古代有关义利概念的基本印象,似乎不大容易理解“以义为利”的含义。学者黎鸣有一个极端的说法,义利之辨是2000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大陷阱,因为用义与利辨,无论义胜,还是利胜,除了两败俱伤,全都有害于人生之外,别无他获。
秦汉以后,延续儒家这套思路者不可胜数。举一个例子,宋代的叶适一贯被视为功利一派,他的见解足以证明儒家说功利,一贯都是以义为利的。叶适的看法是,治国理政,一般人都是讲兵讲利、夸当世、重狱讼、强调行政管理;孔孟之道却是讲义、讲去兵、讲尧舜三代、讲礼乐、重教育。孔孟义理常常因此而被视为迂阔。可是大家自以为是的功利办法,历史证明了,根本不能久长,反而是被视为迂阔的,长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他说:“故臣之所甚患者,以上迂阔诮其下,而下亦苟讳其迂阔之名,自贬而求容于世。其小者,学通世务,则钱谷、刑狱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纷乱,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复行者勉强牵合,以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败事。而臣以为必得其迂阔者而用之,天下其几乎! ”他希望大家能真迂阔些,真去讲孔孟之道,以此大义,兴国之利。
可以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明代邱编撰的《大学衍义补》是一部教育皇帝的教科书,其中涉及义利之辨者甚多。如该书卷二五引用《王制》:“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 ”
而后引用宋代李觏的论述:“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伪盖其常心,矧兹市井,饰行慝何所不至哉?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岂惟愚民见欺耶?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 ”
邱的评注是一句话:“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 ”这个评论耐人寻味。
那么,治国理政之下,古代日常生活层面的义利观,又是怎样体现以义为利的儒家理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