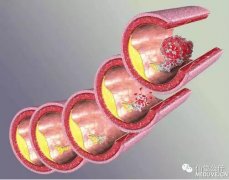我们敬爱的爸爸——任弼时,把整个一生无私地贡献给了人们的革命事业。凡是和爸爸在一起工作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就是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
爸爸平日总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就是得了重病也不肯休息。因为他曾经两次被捕入狱,受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酷刑,加之长期的艰苦革命斗争生活,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不考虑自己。一九四七年,蒋介石调了大批军队重点进犯延安,当时我们的党政军民都做了战略转移,环境十分艰苦。这时爸爸的血压上升,健康状况不好。他担心毛主席知道他的病情会要他休息,交代医生不要反映他的健康情况,他不顾疾病缠身,坚持和周副主席一道,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北京解放后,一九四九年四月,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爸爸在会前带病做筹备工作,对团的工作纲领、团章和文件,都亲自审批、修改,开会时出席大会做政治报告。报告做了一半,他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好让别的同志代替他读,并坚持开完了大会。
一九五〇年,爸爸从莫斯科治病归来,病没有痊愈,血压还很高,他不肯休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医生嘱咐他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越过四小时,但他常常要延长工作时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工作更加紧张,爸爸就夜以继日地工作。这时,他的病也加重了,有时头痛得厉害,便叫我们姊妹帮他擦点清凉油、掐掐头皮,又继续看文件,思考问题,就在逝世的头天晚上,还在看朝鲜地图。爸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工作精神,深深地教育着我们。
爸爸为别人想得多,为革命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总怕麻烦人。进城以后,我们住在景山东街,房子比较狭小,紧挨着马路,爸爸的办公室离马路才两三米,车辆行人川流不息,嘈杂声音很大。组织上为了照顾爸爸的工作和休息,要给我们搬家。爸爸了解到为了我们家搬迁,要把一个机关迁走。他说:“搬家要用很多的钱,而且还要另一个机关让出来,一个人怎么好去影响一个机关呢。”为了避免给那个机关带来麻烦,坚持不让搬家。后来组织上准备把我们住的房子修缮粉刷一下,他说能将就着住,就不必整修,免得给组织上和同志们增加麻烦。就这样,我们在景山东街一直住到爸爸逝世。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进城以后,爸爸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生怕用钱多。在生活上从来不准为他搞特殊,每月都要问妈妈菜金有没有超过标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的。
爸爸还经常教育我们爱护国家资财,节省开支,勤俭持家。我们到北京不久,有一天,妈妈叫我们把一些旧衣服找来做鞋底,我们就把还是在解放区时发的破衣服从包袱里翻了出来。爸爸看我们在翻包袱,走过来一件一件地仔细翻看我们挑出来的衣服,并且从里面挑出两件破得还不太厉害的对我们说:“这还可以补一补再穿,进城了,我们还要注意节俭呀!”
在西柏坡的时候,有一天傅钟伯伯找爸爸汇报工作以后,爸爸留他在机关小食堂吃饭。其实小食堂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好菜,只不过除了几个小菜之外,还另外加了一盘豆腐。当时开这样的伙食就要算是对领导同志的照顾了。傅伯伯看见我们在身边,就要我们同去小食堂吃饭,爸爸不允许自己的小孩去享受首长待遇,硬要我们回家去吃饭。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