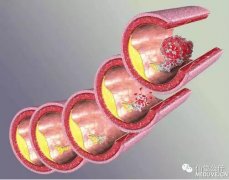当弋舟以“刘晓东”为叙述人讲述故事时,我以为,他找到了他作为小说家观察世界的坐标。《刘晓东》由《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三个故事组成,主人公刘晓东是画家、知识分子、教授,也是自我诊断的忧郁症患者。——忧郁症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普遍的疾病,而弋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透过这个中年男人的内心书写我们时代人的困惑。
忧郁症患者是弋舟小说最重要的符号,或者标签。忧郁症患者思虑过度,忧心重重,他们患有思考癖和追问癖,是“内心戏”极重的那种人。表面上看,这些人面容平和,在人群中常常沉默;但是,了解他们的人会知道,他们的内心常常万马奔腾,翻江倒海。忧郁症决定了刘晓东是一个疏离的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不入戏的人——即使身在其中也常常出戏的人。
潜入忧郁症患者的内心深海
在这三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刘晓东有穷追到底的性格,即使那件事与他无关。他要去找那个突然失踪的青春期男孩;他要帮助那个受伤害的女孩子;他要找到那个死者的前妻或情人,聊一聊突然赴死的主人公。——刘晓东对世界和他人有强烈好奇心,他认定所有人身上都有一个谜底,找不到谜底他不甘心,不罢休。
因而,每个故事中,刘晓东都在追索一般人不感兴趣的问题:即“为什么”,或者“何以如此”。——为什么那个男孩子要杀人?为什么那个女孩子要勒索?为什么那个人决定赴死,不再苟活?穷追不舍地提问会被读者认为“想太多”,但对于“这一个”刘晓东来说,却是有说服力的。因为他是忧郁症患者。
因为忧郁症,刘晓东成为具有某种内在性特征的人,这有利于写作者开辟这个人物的内心疆域。读者也得以潜入刘晓东内心深海。
换言之,正是因为忧郁症,刘晓东这个人物本身具有了“表意系统”,他本身就具有自我阐释性,他的内心世界由此打开。
在变动时代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刘晓东内心分裂。他的成长、他的社会经验使他分裂。时间之河横亘在刘晓东面前。这条河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它把一个人分成两个,一个以前的“我”,一个现在的“我”;或者说,一个以前的他和另一个现在的他。几乎每个人都从这条河中泅渡。一些人虽然渡过去了,但像被扒了一层皮,灰头土脸,片甲未留;另些人也渡过去了,成功变身,如鱼得水。在弋舟那里,80年代是会变魔术的盒子。每个人都从那里走过,那儿是一切的起源。
看起来,《刘晓东》中似乎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成功者,一个是失败者。虽然这对时代和人的理解有过于简单之嫌,但是,书中对成功失败的判断标准说服了我们。——在忧郁症患者眼里,有些人似乎成功了,但他们已经死去;有些人失败了,但他们活着,是痛苦地活着。刘晓东不断回溯他的过往,也不断为他遇到的每个人追溯他们的过去,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时代面前巨大的内在性焦虑和罪感。
尽管我并不同意叙述人对八十年代的浪漫理解,也不同意他对历史节点的某些认识,但是,作为读者,我要坦率承认,弋舟使用一种以80年代为界的划分时间的方式获得了他理解时代的视角。他对刘晓东历史和生活经验的追溯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个病人,理解并同情他的一切,这样的书写也最终使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融为一体,人物性格决定故事走向,而不是故事走向决定人物性格。正是触及到人物的过去和来历,小说家为我们勾勒了一代人的精神轨迹,在变动时代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路历程。
一个独特的汉语使用者
世界上有一种小说家,可以把语言去魅,尽可能丢弃语词身上的历史性、地域性;而另一种小说家,则将简单的词语增魅,赋它们以历史意义及隐喻色彩。弋舟是后一种小说家。从汉语言的基金中,他尤其擅长提取具有精神性意义的语词。一如在《刘晓东》这里,羞耻、罪恶、孤独、痛苦出现频率极高。这些词语有精神性色彩。事实上,刘晓东还常常说出诗歌、理想主义以及爱情这些分明“落伍”的词语。要知道,这些词语连接过去,也连接现在,它们深具历史含义。
使用哪些词语表达,用这个而不用那个,用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言说都是面对世界的态度。——我们时代是对语言极为敏感的时代,但也是语言环境极为粗糙的时代。一些词慢慢死去,被我们无情抛弃;一些词突然出现,我们不得不接受它们,即使它们看起来很恶俗;还有一些词我们避免说起,即使我们内心确实渴望使用,但我们也主动遮掩,以此来确认不落伍。——作为汉语使用者,弋舟深具独特性。他坚持使用一些现在我们不愿使用的语词,他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潮流的不认同、不苟且。他不断地使用孤独,罪恶,理想——这些语词在他的文本中使用频率很高,以至于我们都觉得是不是太多了。并不是太多,很可能是我们遗忘太久,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些词在这个时代本该有他存在的必要,尤其是在作家的词库里。
依我看来,以忧郁症,以对八十年代历史的别一种回溯,以他对汉语言的独特敏感力,弋舟使“刘晓东”成为我们时代病理的切片、我们时代病症的镜像,这是属于弋舟的文学贡献,籍此,弋舟成为我们时代别有追求的写作者,一个需要当代读者重新认识和评价的新锐小说家。
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