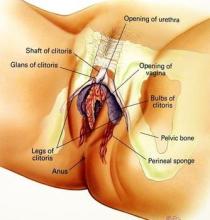为“奇女子”之“奇”正名,张竞生可谓个中之最,对报章所载余美颜种种事迹或传闻,皆目之为奇——她短褂匹马,逍遥广州市上,至于被公安局所禁,一奇也;在香港客栈“出浴返房,一丝不挂”,致被港绅仇视,二奇也;挥金如土,三奇也;奴蓄男子,四奇也;逃入佛门,五奇也;蹈海自尽,愈觉其奇妙无穷——而对凡此种种之奇,更认为“实有伟大的价值”!并以西方价值观为佐证——在那个时代,是足资佐证的:“可惜,她不生于欧美,则短褂匹马,不但免为公安局所驱逐,而且得了‘女英雄’的徽号。又可惜她不生于日本,则浴后不衣而返房,干卿何事!至于挥金如土,更觉可儿。据说被其诱惑者数千人,可见其迷力的伟大无比。取浪子之财,供美人挥霍,故我说她真是可儿也。”?(《“奇女子”余美颜蹈海自尽竞生》,《情化》1928年第一卷创刊号,61-62页)
后来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此际正领导着上海任银行业工会,且曾大力支持北伐战争的章乃器,在其去年11月创办《新评论》半月刊连续发表评论,正面评价余美颜,乃至于大唱赞歌。如陈走崖的《论余美颜》(《新评论》 1928 年第十二期,35页)说:余氏是一个纵欲者,但也是旧礼教的反抗者,同时也是旧礼教的牺牲者。背夫而逃非其罪,恋爱情人无不对。遗书谓误解自由,其实是真自由者。纵欲也非其一人之过。我们除了佩服她的勇气之外,只有惋惜。惋惜她没有真正的爱人,惋惜她行动出轨。章乃器甚至亲自上阵,将余美颜的行为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更符合当时的主流话语:
余美颜在现社会道德的信条之下,当然是一个堕落者。但是她的堕落,完全是环境造成的。倘使她起初就能够得着一个美满的配偶,我敢说她就不至于堕落。倘使她在过她的独身生活的时候,社会上没有一班以女子为装饰品而同时肯化钱去置办那装饰品的人,她也不至于堕落。
怪诞不经的性行,往往不过是环境刺激的反应。倘使一个人照了社会的信条做去经过相当的时间而仍得不到一般人的谅解,同时又得不到应得的成效,自然就会因为愤恨的缘故而照一般人以为是“倒行逆施”的方法去做了。这是很自然的应有的反动。
余美颜之所以自杀,近因固由于恋爱挫折,而远因则由于新旧思想的矛盾。她的绝命书上把“背夫”“背父”当做自己的“罪大恶极”,可见她一面虽然觉到非如此不可,而一面却又觉到不可如此。她有了革命的行为,而没有革命的认识。她是犯了“不知而行”的病。(章乃器《关于余美颜的几句话》,《新评论》 1928 年第十二期,37页)
无论猎奇抑或辨诬,各方对余美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背景,都未曾提到或者根本不了解。余美颜出生、成长的广东台山,乃中国第一侨乡,由于美国的移民限制,特别是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的严苛形势,俗称金山客在美华侨,要想携妻带子,简直难于上青天。而国内的父母亲人,又无不希望华工出国前成亲,即便已身在国外,也得娶个媳妇,以为种种维系,于是就出现新娘抱着公鸡拜堂的奇景,这在晚清民国的台山四邑地区屡见不鲜。由此造成的人伦悲剧,在一首首《金山谣》中得以呈现:
啊!嫁女嫁给金山郎;
嫁给金山来的皮箱,想有多少箱,就要多少箱。
有女莫嫁金山郎,十年九年不同房;
床柱结了蜘蛛网,灰尘积满半张床。
(琼·菲尔泽《驱逐:被遗忘的排华战争》,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123页)
高颜值、知诗书且甚有心气的余美颜,如何长期忍受这种望不到尽头的苦虐日子?更何况娘家还助纣为虐!关于余美颜身世行实,相对靠谱的报道说,“美颜赋性聪慧,口齿伶俐,十龄始就学于荻海女校,娇小玲珑,一目十行,师器重之。不三年,为文已清顺可观。又二年,解吟咏,出口成章,词意天然”。如此,自然好逑者众,而“澄夫(美颜之父)系旧家庭人物,因命美颜辍学,无事不准外出。若辈所施其伎俩,徒呼负负而已”。尔后,贪于金山客的“多金”,棒打她与渤海九少这一对鸳鸯,将其许配于开平的谭祖香,却不料“商人重利轻离别”,“结褵二月,即作劳燕分飞,生离死别,为人生莫大之伤心事,而况远涉重洋,新婚之少年夫妇乎!”而其家婆犹自恶言相向,美颜只有“对镜自怜,以泪洗面”(《奇女子余美颜》,《新银星》1928年第一卷第二期,29页)。
好不容易熬到家婆病逝,得以悄悄离家出走去广州,谁知却无端而罹牢狱之灾:“美颜抵广州之日,即前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之翌晨。当时美颜身穿奇服,行动亦怪,公安局警察以其形迹可疑,便拘入第四区署。”好在她还有一位当县长的姨丈,将其保释并留养。但谭家闻讯,反提美颜之父,保守的余父盛怒之下,追到广州,不把女儿接回,反而虎毒食子,竟向公安局提告其女,令其再陷“牢狱”——判入习艺所一年——相当于“劳改”(《当代唯一奇女子》,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5月4日)。这也等于将其推上了“绝路”——在那个年代,女子至此,已是别无选择,除了堕入青楼,大概还是堕入青楼——以余美颜这种激进的另类方式。
对余美颜的遭遇,沪上媒体基本持悲叹的态度,而粤地的媒体继续保持猎奇的小报趣味。比如,《天趣画报》在1928年第二、三、四期,连续三期以《浪漫之奇女子》为题,刊登其倚椅全裸照而不置一辞,实属恶趣。《珠江》杂志1928年第二十一期刊发了红蔷薇发自香港的《奇女子蹈海始末记》,所附余氏遗照,眼含忧郁,气质动人,然行文格调犹是小报趣味,因而其所谓首刊之遗书,也令人难以置信。在两地纷纷搬演的奇女子故事中,上海这边偏重感慨警世,如著名的广舞台新编的《广东奇女子余美颜投海记》,就颇动人(详参《申报》1928年6月9日二十七版报道)。神仙世界男女剧社排演的《浪漫女子投海记》,也是连演月余,颇受欢迎(详见《申报》1928年5月14日至6月26日二十三版的各期广告)。北四川路老靶子路的上海大戏院也排演了《风流奇女子》,并招徕学界中人观场——“优待学界每座两角”,可见品味不俗(《申报》1928年6月9日,二十六版)。而广州新景象戏班排演的《余美颜投江记》,虽由一代名伶薛觉先主演余美颜,不知是广州当局保守过头,还是戏班真有嫌“下作”——“演至强迫离婚另寻夫婿一段,随意恋爱,淫荡不堪入目”,竟遭禁演,以维风化,而且措辞极严:“倘敢抗违,定予严惩不贷。”(《梨园杂纪:禁演余美颜投江记》,《海珠星期画报》1928年,八期)
传奇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