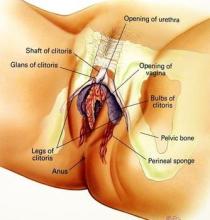奇女子余美颜之遗彩(朱家麟《大亚画报》 1929年第一百五十五期,1页)
1928年4月19日午夜二时许,因在穗港一带放浪无羁十余年而有“奇女子”之称的广东台山籍女子余美颜,由香港乘坐加拿大皇后号邮轮赴沪,在途经温州海口时,从容投海身亡——留下了遗书、遗函及“告妇女界同胞”的公开信,于公于私都甚有交待。正是这些从容的遗留,引发舆论的关注甚至炒作,当然包括大报大刊和“大人物”的评论,从而使得这位“奇女子”之“奇”,由先前基本属于负面的“离奇”,一变而为特立独行的革命之“奇伟”,也正应和着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的主流话语。
有别于政治上的革命性,余美颜的故乡广东在文化上甚为保守,她的“奇女子”故事,主要存在于坊间传闻及市井小报,像《民国日报》这样的报刊所载甚少;像《珠江星期画报》前此一年所作的长篇连载《稗官新著:奇女子外传》(太璞著),捕风捉影,绘声绘色,实属荒谬低俗,令人难以卒读。至此,舆论场则更是完全转移至沪上——穗港前此不多的相关报道,徒充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报章的背景材料而已。
《申报》先行
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待到邮船数日之后抵沪,并将余美颜蹈海的消息按法律程序呈报有司,沪上首屈一指的《申报》始于4月24日第十五版“本埠新闻”刊发报道《浪漫女子深夜投海——恋爱不遂行动乖异,遗书至女界同胞》,虽托言采写自乘客,然所叙十分翔实,如说其所乘船舱情形,便十分具体:“伊由港向兴昌轮船公司买大餐楼船票二张,与女友分住八十九及九十一两号房间,船票银共洋三百六十元。”由此大大增强了报道的可信度。至于其投海缘由,自非一时半刻能得究竟,故仅在其致女界同胞书之外,略叙其身历而已。《申报》并全文刊发其《致女界同胞书》,倒颇显词采风流,且足以动人警世:
颜不幸生于此青黄交接时代,自小凭媒妁之言,听父母之命嫁夫远适外国,数年未谋一面。少识之无,误解自由,竟堕落而任性妄为。在此污浊万恶之社会,浮沉十载有奇,虽阅人甚多,终未能结陈朱之好。前虽钟情渤海九少,山盟海誓,务达比翼,奈为家长所阻,终失所望。既无人生乐趣,留此残生,亦无所用。决然立意毕命,离此污浊世界,还我清净本来。我佛慈悲,当肯援吾魂以归正道也。回忆前事种种乖谬,罪不容诛。上违父母之命,背夫私逃,开女界不敢为之风,而行女界奇耻大辱之举。一思前非,万死不能蔽其辜。但今已如大梦初醒,非死无以赎其前愆,亦无以唤醒女界各同胞也。颜既饱受社会之痛苦,孽虽自取,但亦由社会所造成,愿诸姑姊妹勿以颜之丑行而相为提倡,当以颜为女界之罪魁。今虽身投浊流,亦不能赎罪于万一也。望女界同胞等有如颜之行为者,急宜猛醒回头,早登彼岸,勿蹈颜辙,而取不良之结果,贻万世之羞为幸。语云:一失足便成千古恨。颜事已矣,与世长辞,望吾女界同胞急起直追,唤醒群众,勿再蹈颜之不良结果为幸。
在稍后的报道中,才根据广州《国民日报》等早期的报道,补充描述了一些奇闻佚事。如余美颜因驰马市廛,被拘至警署,处以五圆罚金,便掏出十圆大钞,弃置而去。更令人惊诧的是,她曾于炎热夏日,赤身裸体横陈于酒店卧室门口,旁若无人,谈笑自若。凡此种种,不仅为广州官厅所不容,避往香港,复不见容,于是辗转来沪。又说她自认曾与除土耳其外的三千世界各国男子交接;粤中某局局长与其春风一度后,被索金二万之巨,以无凭无据拒付,余氏便扬言说:某氏下部有一黑痣,便是铁证,如不允所求,当相见于法庭。这个可怜的局长只好如数付款。因此得以挥金如土,到手辄尽——“总其一生挥霍,为数约一百三十万金,诚令人闻之咋舌焉。”(万花《余美颜遗闻》,《申报》1928年4月28日,十七版)
补充报道纷至沓来,关于其遗物的报道,颇可想见其人——其品质之讲究,不可徒目以为荡,实可目以为奇。所遗服饰,均是质料高贵,缝工极精。特别是衬衫一件,“制有淡青莲色软缎,纤腰窄胸,想见绰约身材,展览之余,犹觉脂粉撩人,如乍出红闺者也……昔日红妆青骑挟缰绝驰之浪漫性情,睹其遗物而益信矣”(《劝君莫惜金缕衣:奇女子余美颜之遗物衬衫…女舄…襟花…发网》,《申报》1928年5月4日,十五版)。

“奇女士最后的纪念。与其女友合影”(《新银星》1928年第2期,29页)
其实,前此近一年,余美颜亦有来沪;《申报》的报道虽然只是提前报道了余有意来沪的消息,但其引述自港访沪者之说,对余美颜在港情形、来沪缘由,言之甚详,令人读之有如亲历,殊胜穗港的报道——其中所谓“字头友”,即今日俗称的黑社会大佬:
奇女子者,即粤中大名鼎鼎之余美颜女士也。余女士举止阔绰,装束入时,且为交际界名花,以是人多以奇女子称之,而女士亦自承焉。日前由粤抵港,朋辈为之洗尘,大有山阴道上之概。日出入于各大旅社,引起港政府之注目;先由华民政务司派役传署问话,继由警察司派探传署问话。闻传问之最大原因,据警察方面言,渠与一种俗称字头友者,往来不绝,恐其有妨本港治安,故加以警诫,非欲与之为难也。
下面详叙其与警方周旋,时间地点等,俱言之凿凿,颇资增信。周旋到最后,余氏反诘警方说:“我在港未犯法,何故屡加干涉?今后如余再来港,当如何?”警方回答:“如不犯法,固可自由,惟汝须自慎,勿与字头友往来可也。”虽不复限制其自由,但仍限期出境。故有“闻女士已购定船票,准备来申,且一般洗尘者,又纷纷为之饯行云”(杏雨主人《行将来沪之奇女子:亦是情场失意人,闻欲显身沪银幕》,《申报》1927年7月1日,十六版)。
可惜沪上报纸对其到来竟未予跟踪报道,不知何故;待其蹈海之后,始见民国以研究性学著称的网红级教授张竞生博士在文章中提及:“连日在民众日报及青光上看到奇女子余美颜的蹈海自杀消息,使我有无穷的感慨。当去年这个奇女子来上海时,我友偶然与之同行,到上海向我说及‘你是否要一看奇女子’,我漫应之,而终于无缘得见一面。距今不久,又有一友向我谈及外间说我与‘奇女子’定然会过。我誓言未曾。他说这真可惜,即自优先权为介绍人。翼(翌)日来说她已往香港好久,候其来再图谋。殊知‘奇女子’竟蹈海而死了!”?
沪上誉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