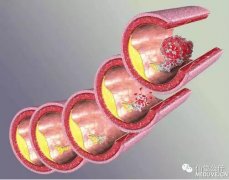3
因为服药方式错误,在最初几年,一套治疗方案用上1~2年,孙明娟体内的艾滋病毒就有了耐药性,不得不换新的方案。每次产生耐药性,她的肾病就会反复,还伴随着高血糖、高血脂等一系列并发症。
2009年,她因为艾滋病的并发症,开始用激素辅助治疗。2011年,她又产生耐药性,用上了医保范围内的最后一种药物,但那给她的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直到最近几年,孙明娟的病情才平稳一些。
她的日子过得格外谨慎,出门时戴口罩,尽可能不坐公交、地铁,不出现在人多的场合。身边一有人打喷嚏,她就紧张得不得了,赶紧回家吃感冒药。每到流感季节,她都疯狂喝水。
恢复上班后几个月,孙明娟的脸就瘦尖了,双脚却肿得穿不进去普通的鞋,每天只能穿拖鞋出门。
复诊见到李太生时,他生气地说,“你离我这么近,出这么大问题不来。”一名护士看到她惊呼,“你不要命了!”
她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撑她做一份平常的工作。她本以为自己瘦是因为辛苦,却从李太生那里得知,这是抗艾滋病药物的副作用,她的脸永远都不可能恢复了。下巴和颧骨处的肉都萎缩了,能看出骨头的形状。
一起萎缩的,还有她的理想。“以前我还想出人头地,挣多少钱,(现在)都没了。”她辞掉了工作,回家休养身体,“还是身体重要……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太丑了。”
药物还让她健忘。到北京随诊,她好几次等车或坐车时忘拿行李。去超市买东西回来,她总是忘记东西放在了哪里。
2011年,药物让她掉光了头发,肾病再次变得严重,还伴随着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青光眼。护士给她测血糖,高到机器都“爆”了,测不出来。
一次,因为吃了两个包子,血糖飙升,她被医生批评,“你怎么能这么吃?”之前一直强作镇定的她在病房里号啕大哭,“我怎么活成了这样,连两个包子都不能吃”。
她不得不用上当时医保覆盖的最后一种药物,但那会给她的肾增加负担。而且如果再一次产生耐药性,她将不得不自费购买进口药物,每个月花费数千元。后来,赶上“十二五”规划,孙明娟用上了国内尚在试验阶段的疗法。
症状稍稍好转,她又被夺走了独自行走的能力。药物让她的双腿肌肉萎缩,股骨头坏死,走路“从脚后跟连到大脑地疼”。做活检需要从大腿上挖一块肌肉,她疼得几乎晕倒,当场就觉得这病不治了。
地上几厘米的小坑就能让她摔倒。她家在五楼,每次上楼都要花费半小时,一路跌倒,完全靠抓着扶手才能回去。
有一次她想自己去菜场转转,都走到跟前了,地砖的不平整让她跌倒在地。她向路人求助,却没人敢扶她,让她给家人打电话。她不想麻烦家人,最后一点点爬到路边,扶着树才站起来。
到协和看病的时候,她的脸色非常差,不断咳嗽,一度意识都不清醒了。李太生还是和往常一样,告诉她“你很好”“没问题的,别担心”“你这种情况我们都治过”。事后才知道,那一次李太生真的担心她“过不来”。
医院检查结果说孙明娟双下肢神经受损。“既然没说坏死,就还有恢复的可能。”于是她每天到小区里蹬健身器材,光路上往返就要一个半小时。冬天天黑得早,老头老太太都回去了,她一个人顶着寒风锻炼。一开始她只能蹬3个,后来,她一次能蹬300个,每天都坚持。
后来在李太生的协调下,她又在协和医院做了股骨头置换手术。2014年医保多覆盖了一种抗艾滋病药物,副作用更小,李太生便给她换了药物。
每一次治疗走进死胡同,她都幸运地赶上新的项目和疗法。她总是因为病痛紧张得睡不着觉,“很奇怪,每次见到李大夫,他都轻描淡写地说能治,我也都相信了”。还有护士向她打趣,“李大夫就是你的新药。”
她依赖了这个大夫15年。在家嗓子疼,她一个电话打到医院,护士接都不行,一定要李太生接电话。李太生出国开会了,她就住进医院等他回来。
每年夏天过完,她就开始忧心,自己能不能挺过这个冬天,甚至几次想过写遗书,“要好好把自己对父母的歉疚说出来”。天冷起来,她又想到春暖花开的样子,便给自己打气,一定要撑到那个时候,出门看看新生,“多活一天就赚了一天”。
李太生不止一次感慨,在孙明娟身上看到“生命真的很强大”。他掂着孙明娟大腿的肉,“你看这就是生命力。”孙明娟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现在长胖了,头发比年轻时候还要浓密,糖尿病、青光眼……种种不可逆转的疾病,“到我身上居然都好了”。
孙明娟有个堂姐,30多岁因车祸去世。每次亲戚见面,姑母还是会哭得不成人样。当时姑母和孙明娟说,你虽病着,但你父母还是能见到你。即使难过,也不是天人永隔的痛苦。
她说,是这句话一直支撑自己活到现在,“我得让父母看到我,我要在他们的视线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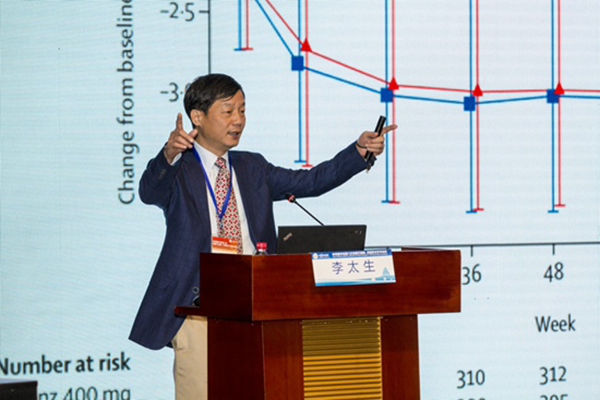
4
艾滋病的秘密,孙明娟守了15年。
曾有亲近的朋友怀疑过她得了艾滋病,她赶紧把话题岔开。有人也得了严重的肾病,向她打听在北京怎么治的,她只说帮忙问问出不出诊。这些都让她心里发慌。她办不到坦然地和别人谈论艾滋病,“可能大家都说社会观念进步了,但我个人没有感受到”。
就在孙明娟确诊艾滋病那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到北京市一家传染病医院视察,并与两名艾滋病患者握手。结果当日《新闻联播》播出时,他们的脸没有打马赛克。
他们直面镜头,本希望消除歧视,“老百姓会觉得,看,国家领导人都不害怕艾滋病病人,咱更不用怕了”,却让全家人陷入了被歧视的境地。
孙明娟在医院听别人说起过这件事。那阵子,走在街上,在医院拿药、做检查时,她总觉得身边的人在议论自己。
在门诊,患者总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医护人员发现,三四十岁的人最谨慎,“外界带来的压力,甚至比疾病本身还要重。”他和护士有时在医院附近的商场遇到病人,都当作不认识,从来不会主动打招呼。
对艾滋病患者来说,身份暴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丢掉工作,有的连生活都过不下去,后一步才是亲朋好友歧视带来的伤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多部法律都规定不得歧视HIV感染者,但患者维权成本极高,耗时长。
2010年,中国首例艾滋病感染者就业歧视案中,安徽当地法院驳回原告(患者)全部诉讼请求;次年发生在贵州的一起艾滋病就业歧视事件中,法院不予受理。一直到2016年,中国才迎来首例获得法院判决胜诉的艾滋病就业歧视案。
2008年,李太生提出,应该把艾滋病当作一种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进行治疗。在他们长期随诊的1500个病人里,过去七八年,死亡的病人只有9个,7个死因跟艾滋病无关。
他还记得,刚回国时,有同行知道他在国外学的治疗艾滋病,都不和他坐在一张餐桌吃饭。
目前,仍有很多医院拒绝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他们不会明说,但就给你拖着,或者采取保守疗法,只吃药,不开刀。”李太生说。
“现在医疗资源紧张,绝大多数科室不缺病人,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更何况是艾滋病人。”
他能理解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上世纪90年代在法国学习时,他也很害怕。第一次碰到患者的皮肤时特别紧张,感觉“凉凉的”“像蛇一样”。但是他学习的医院里,很多医生上手摸艾滋病人从不戴手套,看完病人后,走进咖啡屋,手都不洗拿起面包就啃。
在他眼里,艾滋病人反而是最容易沟通的病人群体,他们大多很听话,态度也很好。
从查出艾滋病算起,花了5年,医院才肯给孙明娟做肾穿刺。她是协和最早做肾穿刺、股骨头手术的患者之一。当时,李太生完全靠私人关系,说服了主治医生、麻醉医生、相关护士,才让手术成行。次数多了,一些科室就不再排斥艾滋病患者,从感染内科转过去做手术成了家常便饭。
李太生觉得,宣传还是很管用的。在10年前,很多人都认为艾滋病是绝症,不会去看医生。他还经手过一对夫妇,把孩子送给了亲戚,把老家的房子和地都卖了来北京看病,打算看看天安门就等死了。
结果病情控制得很好,他们冬天卖煤球,夏天养猪挣钱,把卖掉的房子和地又挣了回来,孩子也接了回来。现在,来看病的人已经很少会认为自己没得治。
艾滋病在孙明娟的身上留下很多痕迹。因为经历特殊,她简直是一部艾滋病“药典”,住院时,常有外国专家来围观这个“稀有动物”。她被置换下的股骨头都成了重要标本,供国内专家和日本东京大学的专家研究抗艾滋病药物对人体的影响。
在医学以外的世界,作为“活化石”的孙明娟依旧保持着“低调”,她打算将自己的秘密永远保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