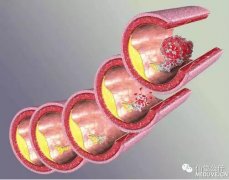一个家庭的冰箱就是一部迷你小说。如果给我家冰箱安上一个个摄像头,它也离奇地参与并记录了我的治病史。
-------------------------------------------------
小丽剃着光头,弓着背躺在床上,像一只被剥了壳的龙虾。她的妈妈正在给她的小腿裹保鲜膜,小腿上有着地图状的红斑,因为抹药的关系,红中透亮。
4年前,这是我第一次见小丽。小丽是一位银屑病患者,我也是。
她刚上初中,我上大二。在北京一家皮肤医院走廊尽头的病房里,我们穿着一样的病号服,吃一样的病号饭,我们的身上都有银屑病结的网。
少女的双腿因为肿胀无法动弹,得由妈妈背上背下。更多的时候,她蜷在床上玩手机、打游戏。她声音洪亮,我早她一天到医院,她大声向我咨询住院事宜,也因为我独自在医院,而对我投来关心。
相比小丽的病情,我则要幸运得多。病人间的比较是可笑的,也是伤人的,我暗自放在心中。面对疾病,我们都是那只束手无策、任人宰割的小绵羊。
就医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药浴、打空气针、紫外线疗法,间歇中穿插着吃药、打点滴。这家医院是我妈妈从电视中看来,极力推荐我去的。
小学五年级,我的额头上出现一块红斑,指甲盖大小,覆盖着白色鳞片。15年来,它们像长了脚的蜘蛛,从我的额头转移到后脑勺,再到颈部和背部,在我的皮肤上结网。
这是被确诊为银屑病的皮肤病。我及爸妈被清楚地告知,这是一种慢性的、非传染性的皮肤病。它无法治愈,且遗传后代。
银屑病是个擅长隐蔽的高明杀手。它潜藏在我的头发里,背部又被衣服遮盖。很少有朋友知道我得了皮肤病。而它的嚣张在于向世人发出挑衅的信号——白色的鳞片。它们更像是头皮屑,落在我的肩头,夹在发丝里,还有被抠烂的红斑,白衬衫上的点点血迹。
作为患者,我无法拒绝疾病,和解的方式只有治疗。书包里常年放着棕色的药片,一口水吞下十几粒,睡前调和膏药涂抹在患病处。
令妈妈崩溃的是我不配合。不按时吃药,不坚持看病,任何一项都能令她哭泣。有时,她还在上班,我就接到妈妈的电话,哭着命令我吃药、抹药。她害怕,我因此毁容。
甚至,晚班回来,她悄悄摸进我的房间,看我是否听话抹药。慢性疾病从不是一颗子弹,瞬间结束人的性命,它在你的生命里游动,不声不响,却又有千万只蚂蚁在爬,赶也赶不走。时间长了,我也恍惚,是不是多了一个朋友,那种常令人气恼又甩不开的牛皮糖。
甩不开的痛苦如影随形。我的眼神随时瞄向肩头,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用手扫过肩头的白屑。衣柜里的白色衣服越来越多,这能令我放松,不再保持警觉。初次和一个女孩成为朋友,是她看见我肩膀上落的白屑,开玩笑地说着“这里有头皮屑”,一边轻松地帮我拍掉。熟悉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她会扳过我的身体,看最近病情是否严重。
作家苏珊·桑塔格的经典著作《疾病的隐喻》,试图“将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那些隐喻影子进行彻底曝光,还疾病以本来面目。”
她从认知上呈现疾病的本来面目,给患者“洗白”。在社会语境中,我感谢这种“洗白”。而回归个体,疾病是私人的,痛苦也是私人的,肉与灵躲在疾病的阴影下瑟瑟发抖,不敢伸张。
一位病友对外称自己是过敏。当我们相约一同去看病时,在场的另一位朋友开玩笑说,“皮肤病和性病都是一个门诊室。”我看到她脸色一变,嘴角下沉,隐隐地不满。
多数情况下,我会向朋友坦白,解释这是一种皮肤病。这源于我妈妈的态度,她热情、爽朗,她做服务工作,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打一声招呼就可以攀谈起来。她毫不避讳地谈起很可能令女儿毁容的疾病,如果有什么妙方,隔天就会实验到我的脑袋上。
她也是最着急的,我开始发病的时候,家中一本银屑病的科普书已经被她翻烂,粘着油渍、水印,背面记着密密麻麻的电话和地址,那些她从电视、报纸上看来的“神医妙方”。
我看过一回“神医”。看完病后,家里的冰箱塞满了熬好的中药。但我一喝中药,就开始拉肚子,才没有继续吃下去。
我还用过一种树干的汁液。暑假的早晨,妈妈带着一把斧头骑车出门了。那种汁液是白色的、略黏稠。我坐在小板凳上,呆头鹅一般伸长了脖子,她把汁液涂抹在皮肤上。
之后还用过烟草水,从家乡寄到北京,身上第一次有了烟草味。假期回家,打开冰箱,又是一瓶一瓶烟草水。我曾经想,一个家庭的冰箱就是一部迷你小说。如果给我家冰箱安上摄像头,它也离奇地参与并记录了我的治病史。
这几年,我和妈妈爆发的几次“大战”,都是因为我的病,那成为她心头的痛。在贴吧,她看到香港有一种疗法,据说治好了不少人。妈妈抄下医生的姓名地址发给我,甚至同我商定好去香港的时间。
当然,她看到了疗法,并没有看到潜在的风险和复发的可能。对于立竿见影的方法,我都有着警觉。
但是,妈妈并不会意识到这些。“一定可以治好,网上十来个人都这么说,这个医生很有名。不管花多少钱,你去,不要让妈妈伤心……”妈妈的嘴皮子上下翻动,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这几句反反复复地向我砸来。
小丽弓背的样子在我脑子里晃,有时,我会想到她。我出院的那天,存下了她的电话,但是我们再没有联系过。这些年,她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偷偷哭,妈妈还抱得动她吗?
她会因为红斑,而拒绝爱情吗?未来如何向另一半解释银屑病以及随之而来的遗传可能性?她会悄悄藏起皮屑,躲避别人异样的目光?她也会被人大剌剌地拉开衣领,高声点评么?
我的职业是媒体人,观察各种社会关系的编织与解构。15年里,我与银屑病朝夕相处,却是一再忽视我与它的关系。
疾病留给我的,已经超越疾病本身。
我知道在海南有一家医院,被媒体描绘成银屑病患者的天堂,坐在海边晒太阳,泡海水,还有从五湖四海而来的病友。被疾病区隔离的孤岛,遇到了另一个孤岛,我们发出了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