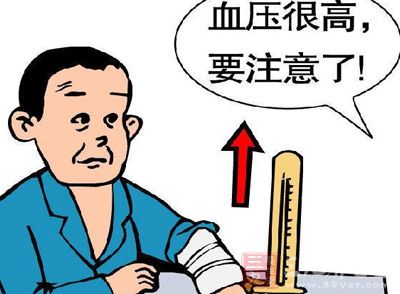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