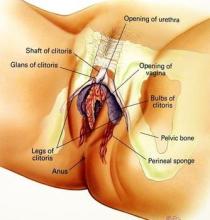1
有东北人的地方,从来不缺笑料。
东北话抑扬顿挫,多四字拟声词,擅用比喻、夸张、场景描述、自我嘲讽,包袱抖得咔咔直响,常常让人猝不及防。
当局者迷,身在其中时多半不知,但只要在别处待过一段时间,再回到东北,就会被东北人全民普遍的幽默感一击即中。于是回想起从小到大,从家人到朋友,老师到同学,无一不好笑,差不多都贡献过够笑一辈子的笑料。
或许是长时间的严寒太让人绝望,围着火炕磕着瓜子儿唠着小嗑的欲望深埋在东北人的基因之中。不管是路边等车,打出租车,还是公交车、火车上碰见,哪怕只是一起上个电梯,在水果摊挑个水果,在商场挑同一款衣服,他们都能随时随地开聊,迅速熟络得像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谈话很快变成抖包袱、甩段子的角斗场。有意或无意地,大家似乎默认了——说话不好笑,比如回家去睡觉,不埋梗的磕,简直没法聊。
哪怕是在医院这种冰冷绝望的地方,都有东北人施展拳脚的机会。住在同一个病房里的人,此前不相识,之后不相逢,短短几天几十天,大家毫不吝啬闲聊逗趣,把整个病房变成一个大炕,你抓我一把瓜子,我吃你几瓣儿橘子,互相取暖,挨过难熬的时间。有时遇到高手,一不小心就乐出了眼泪。

父亲隔壁床的大爷因为喝酒贪杯,无酒不欢,把自己直喝到胃出血住院。父亲入院的时候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十几天,禁食整十天,每天靠打营养液维持。点滴打久了,形成血栓,整个左手小臂红肿起来。医生让他用生土豆片敷,然后裹上毛巾消肿。一天,大爷拆开毛巾,在一旁自言自语:“我这还没发烧呢,这土豆咋烤成薯片了呢?”拎起来的一片土豆,看上去果然已经“烤熟”了。“挺好,自己烤自己吃。”
看见我在拆我爹的一次性氧气瓶,大爷又来了主意:“姑娘,你爹不爱钓鱼吗?你给他改造一个氧气瓶,潜水用,不用在岸边钓,直接下水捞,多带劲!”我爹一听,顿时来了兴致,不顾刚手完术,认真地研究起了氧气瓶的构造。我觉得如果给他俩准备点下酒菜,承包一片鱼塘,各自甩上几杆,指不定能聊上一整天。
大爷的幽默不光给我爹灵感,还化解了不少尴尬。靠窗那床的阿姨因为年轻时生孩子打激素,体型偏胖,走路艰难,需要扶着床才能勉强走到厕所,经过时发出吭哧吭哧的喘气声,场面一度尴尬。大爷来一句:“我说你走道儿能不能认真点儿?”全屋十几个人都笑了,有人搭腔:“好像人家没认真似的。”阿姨自己也笑:“没看出我这正使劲儿呢么?”
阿姨虽身型偏胖,闺女可是苗条大个,足有一米七五,在病房里走路虎虎生风。大家就和她逗趣:“你闺女可比你苗条多了。”阿姨不认输,一只手摆弄头发,露出名媛一般的神气表情:“那可不是!也不看她娘是谁!别看我这样,想当年也是一枝花!”
3
我爹从手术室回病房那天晚上,需要从手术床换到病床上来,全屋能动的人都过来帮忙。大爷也不例外,全然不顾自己也是个病人,虽然那时他差不多快要康复了。大家抬到一半,发现大爷也在,忙撵他去休息。我爹刚刚从麻药中醒过来,看见大爷已经自己穿好了衣服,正准备进行术后遛弯的康复治疗。我爹一脸羡慕地瞅着人家,冲人家眨巴眼睛,大爷回头,语气波澜不惊:“去遛弯儿喽!走啊,领你去溜一圈去。外头空气可好了。”我爹苦笑。
这一招儿原本是我爹发明的。
对面床的姑娘A爱吃,常年吃烤肉烤串火锅麻辣烫,自己说“属于无肉不欢型的”,结果年纪轻轻,硬吃出了过度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大夫要她禁食,一段时间内不能再吃多油多盐的肉了。她每天捧着塞进病房的外卖小广告,感叹:“这肉看着就好吃。”大家就劝:“得了啊,再吃就不划算了。”我爹没手术之前住院,一天出去吃晚饭之前,冲那姑娘说:“去吃烤肉喽!走啊,带你吃小烧烤去啊。杠杠香。”
到江湖上混,果然都是要还的。

姑娘A虽然看上去很坚强,其实特爱哭。点滴打到一半,就哭得梨花带雨。家属吓坏了,叫大夫来,大夫也逗:“哎呀我的妈,这咋还给整哭了呢?”姑娘A哭着说:“太疼了。打得太难受了。”大夫劝:“不哭不哭,咱不打了,停了停了。”停药之后,姑娘继续捧着那几张外卖单,望梅止渴,看得津津有味。
姑娘B说起自己是怎么住的院,也颇有戏剧性。“公司食堂吃馒头,人家一人顶多吃一个半个,我能吃啊,一下吃了俩,结果馒头长毛了,没看见,当天晚上就连拉带吐,给我造昏迷了三次。”大家伙儿一惊:“那你洗胃了吗?”“洗了啊,自己给自己洗的,全靠吐。”姑娘B经此事之后,至今心有余悸:“往后余生,打死不吃馒头。”
病房里大部分病人都有人陪床,偶尔遇见没有家属陪床的,左邻右舍就帮忙盯着,稍有情况不对,或者换药拔针之类的,就帮忙按个铃叫护士。57床要换药,姑娘B冲着对讲:“57。”护士没听清:“啥?76?”姑娘B不干了,嗓门高八度:“57!57!57!”撂下对讲,自己在那儿纳闷儿:“57能听成76,我刚才说的是外语么?”她看上去好像真在怀疑自己。东北人一旦演起戏来,一定要演完全套才肯罢休。真真假假,才是生活的真谛,而东北人只是将它浓缩成了精华。
虽然下决心不再吃馒头,但医院食堂的主食实在有限,姑娘B能吃的不多。到了饭点儿,她又开始了她的世纪大困惑:“吃啥呢?不吃,饿,吃了,吐。”有人提议:喝粥。不提不要紧,一提她火更大了:“粥粥粥,每天都喝粥,我都快变成粥了。你看我,我就是一大坨粥!”
5
熟悉东北话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东北话的特定修辞法。小时候和家长要玩具:“妈,我想要个自行车。”妈妈多半会说:“要什么自行车?我看你像自行车!”“妈,我想吃冰棍儿。”“我看你像冰棍儿!”或者,“爸,我想吃烤地瓜。”“你看你妈像不像烤地瓜?”就在我用心琢磨我妈像不像烤地瓜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功结束了。
这个办法对于家长来说屡试不爽,但对孩子来说是个艰巨的课题:为啥吃啥就得像啥?像啥才能吃啥?这个课题困扰了我的整个童年。
在东北话中,没有什么表达是不能用修辞解决的。
有个说法是,东北人相信万物有灵。比如你找不着橡皮了,问你娘:“我橡皮呢?”你娘会回一嘴:“找橡皮你问橡皮去啊,问我干啥?”或者你不小心磕到了桌子腿:“好疼。”“人家桌子都没说疼,你疼啥?”小时候我家楼下开饭馆,蟑螂多,一天,见一只蟑螂从碗柜底下经过,我大叫:“啊——蟑螂——”我爹在一旁给蟑螂配音:“啊——张畅——”
戏不多的爸妈绝对不是东北爸妈。